
图片源于网络
吃人这事,怎么看?
✪ 郑少雄
唯物主义者说,吃人是因为原始人缺乏蛋白质;弗洛伊德的信徒说,吃人是为了满足某种性心理需要;如果有人说,吃人是一种宇宙哲学上的需要,它是世界得以延续的一种条件,这是文化论者。以上林林总总,都是普通人类学者。吃人不但在原始人的社会真实发生过,吃人的观念和实践也在所有社会中以种种或隐或现的方式存在,包括此时此地西方人自己的社会。说这话的人是列维·斯特劳斯(以下简称列翁)。
现代社会居然也在吃人?不会吧,我们可是文明人啊!甘肃白银系列杀人案嫌犯突然落网,围观群众无不欢欣鼓舞,觉得正义终于要得到伸张了。但是且慢,我在新闻下面看到无数评论,建议对杀人狂魔处以最血腥可怖、惨无人道的肉体凌迟,甚至还有要求寝皮食肉的(瞧,我们是食人族吧?)。可见,我们一正义起来就会摇身一变为野蛮人,哪还有半丝文明的影子?
这也正是列翁的主张。在他看来,原始人未必就没有现代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而现代人的观念,也未必就肃清了自己身上的远古遗存,原始人和现代社会人之间并没有区别。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我们都是食人族》,就其总体意旨而言,要说的无非就是这么多。为了达到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从1930年代正式开始研究和田野工作算起,到写作本书的1990年代,列翁花了一个甲子的时光。
归结起来,列翁的人类学关键词是“神话、图腾、亲属关系”,也可再加上“句段、联想、二元对立、矛盾转化”,当然,如果碰巧你还知道“忧郁、无意识、悲观主义”等词汇,基本上可以不必往下读了,你已经是结构主义专家了。
列翁的思想光辉,星星点点地洒满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本书由17篇评论性文章构成,除了篇首“被处决的圣诞老人”以外,其他16篇都是应意大利《共和报》之邀而写,发表于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涉及的话题十分广泛。
以下我将分析其中的几篇,并进一步延伸来勾勒列翁的整体轮廓。忙碌的行外读者在这里离开也无妨,你至少已经知道levi’s不仅仅是牛仔裤了。
神话直指脆弱的人心
《被处决的圣诞老人》写于1952年,是本书最重要的文章。这一年,虽然《结构人类学》(1958年)、以及公认的结构人类学奠基之作《野性的思维》(1962年)都尚未面世,但“被处决的圣诞老人”已经展示出了精妙的联想隐喻,超凡的逻辑推理,可以算是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预告。而文章中显示出来的对人类的深刻悲悯,也足以打动读者的心。
1951年圣诞节前夕,法国第戎教会当着250名孩子的面,在大教堂前以火刑处死了一个圣诞老人模型,原因是圣诞老人的存在,使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异教化”了。这一举动遭到了舆论和普通民众的反对。这里的吊诡之处是,基于圣诞老人可疑的来历,教会的处置体现了一种求真的批判精神,而理性主义者反而看似在捍卫迷信。列翁在此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圣诞老人这个著名的异端会如此泛滥?
表面上看,圣诞节在西方并非久远的事物,但实际上包括圣诞老人、圣诞树在内的各种元素,都是从远古至近世多种多样的来源的综合体。圣诞老人与世界各地定期返回人间的神灵或祖先,在结构的意义上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被生者创造出来,通过回到人间来奖励(有时也包括惩罚)妇孺,完成对社会身份的区分:一种是成人——启蒙者;另一种是孩子(有时也包括妇女)——未开蒙者。如果和美洲大陆的神灵结合起来考察,则有更惊人的发现。比如印第安人中的“卡奇纳”,是意外死亡的小孩的魂灵,他每年都要回到生者的世界拜访,并在离开时带走孩子。在这个意义上,圣诞老人和卡奇纳一样,代表的是死者;他奖励的对象(对卡奇纳而言,是带走的对象)——孩子——实际上也是代表死者。圣诞老人和孩子在结构中的身份是一致的,都是死者,共同与生者构成二元对立。
圣诞节的时间节点,亦有其深意。12月下旬是一年中黑夜最长、白昼最短的时刻,但也正是夜晚渐短、白昼渐长的转折点,表明光明和生命即将得到拯救。圣诞老人将礼物(其实礼物来自生者)赠送给孩子们以后离去,表明死者退出生者的世界,留在生者世界的死者(也就是孩子)暂时获得了安抚,将不再威胁或迫害生者(成人),这意味着生命战胜了死亡。来年万圣节起,以孩子打扮成亡灵或骷髅敲诈成人为象征,死者将重新开始威胁和迫害生者的世界,到圣诞节生命重新获得胜利,如此循环往复。死亡的威胁虽是恒久的,生命也永不停止。
在一神教支配的社会里,列翁通过圣诞老人神话的分析,赞颂了光明和生命,试图为“异教徒”(也就是普通的人文主义者)的社会打开免于死亡恐惧的大门。可以说,任何一个神话分析,不管它隐含的主旨是宏大或是幽微,必定都直指社会人心最脆弱的部分。本书中《作者自叙》也是如此。
《作者自叙》是1991年为《猞猁的故事》出版而作,那也是发现新大陆500周年前夕。《猞猁的故事》与《嫉妒的制陶女》、《面具之道》、以及集结构人类学之大成的四卷本《神话学》,共同组成列翁关于神话研究的皇皇巨著。《猞猁的故事》考察了北美印第安人中关于雾与风的起源神话,猞猁(猫科)是送来雾的人,郊狼(犬科)是捕获风的人。最初猞猁和郊狼不管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就像双胞胎一样,但是后来由于发生怨恨和报复,两个人互相把对方变成了彻底相异的人。这个传说隐喻了印第安人关于二元的看法,那就是二元必须是对反、相异的(猫狗不正是天敌么?),而且这二元并不均等,必定有一方优先于另一方,正是这种动态的不平衡状态维持了世界的正常运作。在二分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印第安人天生就具备“他者”的观念,既然有“我”,则必有“他者”与之对应。印第安人是这样分类的:造物=印第安人+非印第安人(当遇到欧洲人时指的自然就是白人);印第安人=同胞+敌人;同胞=好人+坏人;好人=强者+弱者……也即说,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的观念中早已为他们预留了位置,而且印第安人认为白人的文化比他们更优秀,是造物主真正的儿子。可惜的是,印第安人开放、接纳的态度并没有感化种族中心主义的欧洲人:欧洲人以为自己是上帝创造的唯一人种,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与突然遭遇的他者相处,在美洲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以怨报德。归根结底,美洲的神话说的其实是两种文化接触的故事:印第安人天生崇奉并善待他者,就像萨林斯笔下的夏威夷人,把库克船长当做了神,结果却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列翁说,纪念发现新大陆最好的方式,是欧洲人的忏悔和反省。
看看,结构主义就是这样一门脑洞大开的技艺,把一切枝蔓繁杂的线索都简化为神话素,这些神话素是些两两对立的对子,所谓神话(实际上表征人类的观念与现实世界)就是要素之间对立关系组成的网络。
我们再用一个别的例子来说明。
列翁在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神话里抽取出十多个句段,认为所有句段所体现的,无非是“否认血缘关系”(如俄狄浦斯杀父)或“强调血缘关系”(如俄狄浦斯娶母)、“否定人起源于大地”(如俄狄浦斯置怪物斯芬克斯于死地)或“肯定人起源于大地”(如俄狄浦斯名字的原意是“肿的脚”)这四个神话素,而这些神话素,反映的是自然与文化、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性质对立,这些共时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就是神话背后隐藏的结构。
这一成就,是列翁在分析了上千个世界各地的神话后归纳出来的。过程可谓艰辛、结果亦可谓振聋发聩。这种集体潜意识中的二元逻辑图式,见于一切人类,不管是空间中的我们和他们,还是时间中的今人和古人。
我们都是相同的造物,不是吗?
亲属关系:老娘舅依然重要
在我的童年生活经验中,在我的闽南老家,娶媳嫁女这样重要的礼仪场合,老娘舅必定是坐在首桌第一个接受新人敬酒的人;遇到兄弟分家,老娘舅则更是终极裁决的权威。老娘舅并不是家里人,为什么管我们家的事?
别以为只有华南农村才这样。《母舅复返》提到,戴安娜王妃去世后,她的弟弟斯宾塞伯爵在葬礼上指责了皇室家庭,并重申自己作为舅舅保护、支持小王子们的道德权利。在已经充分理性化了的不列颠,舅舅的结构性角色在重要仪式场合(列翁称为临界状态)突显出来,可见中古时期的某些基本社会原则仍在潜滋暗长。
舅甥只是诸多亲属关系中的一种,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如此受人瞩目?
结构主义关于亲属制度的讨论,仍然是把亲属关系化约成四种最基本的要素:横向的有兄妹(血亲)、夫妻(姻亲);纵向的有父子(继嗣)、舅甥(另一种继嗣)。舍此之外,别的亲属关系只是这四个基本要素的同构或延伸。血亲关系与姻亲关系符合对立原则,也即兄妹关系密切的,则夫妻关系相对疏远,反之亦然;两对继嗣关系之间也是如此。从土著到欧洲人的社会,无不服从这个原则,只是由于我们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一些新的观念和实践(比如核心家庭)的兴起,有些原则被遮蔽,表面上看兄妹关系和舅甥关系已经无足轻重了。被遮蔽并不代表不灵了。《女性与社会起源》、《社会问题:割礼与人工生殖》也有关于亲属关系的讨论,而且更进一步,涉及了乱伦禁忌与社会性亲属关系的话题。简单说,乱伦禁忌就是不能与有血缘关系的人发生性关系。多数人更愿意相信,乱伦禁忌是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列翁也同意乱伦现象曾经普遍存在,但他坚持认为乱伦禁忌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只是在不同的文化中,乱伦禁忌的内容不一样而已。就如我们所知,表兄妹和堂兄妹在血缘远近方面没有任何区别,但是表兄妹结婚被推崇(不管是宝玉和黛玉还是宝玉与宝钗),堂兄妹结婚则闻所未闻。在结构主义看来,原始人从使用图腾来区分部落或氏族起,乃至于更早,就知道必须通过女人的交换、也就是让女人流动起来,社会才得以建立。所以,舅舅是那个“送女人的人”,丈夫则是“收女人的人”。为了保证女人的对外交换,乱伦禁忌自然成为必须,这就是所有的核心机密。
也就是说,在列翁看来,原始人没有存在过所谓的自然状态,天生就是逻辑思维的、理智的、文化的。他们的文化如此发达,以至于他们早就发明了社会性亲属关系的概念。简单说,社会性亲属关系就是我们(可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亲属,但社会和文化认可我们是。比如兄弟共妻家庭中的孩子,都以最大的兄长为父亲,而不深究生身父亲是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方为解决人工生殖(包括借腹、借精、借卵)等科技手段所导致的道德和身份焦虑,实际上在原始社会中可以找到大量可供借鉴的智慧。
原始人比我们更开明、更灵活,也更重视社会的价值。他们通过女人、食物和信息交换,结成了社会。社会的肇始并不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悲观的理智至上主义者
从最直接的渊源来说,结构主义人类学有两大源头,一是结构语言学,二是潜意识理论。结构主义人类学在六十年代出现以后,迅速风靡知识界,乃至成为一股普遍的哲学和社会思潮。但是,结构主义也从不缺乏来自外部的批评。结构主义强调下意识行为,强调社会结构对人的制约,强调文化的共时性,而不是稍早于它的存在主义所强调的人的个体自由和历史的进步发展。萨特批判结构主义有一种把人视作蚂蚁的倾向,但列翁反驳说,他比萨特更重视人的尊严和权利,历史进步观并不能维护一切人的权利。萨特的批判固然有理,但列翁的反驳似乎更符合世道人心。萨特说人是孤独的,他人即豺狼;列翁却反复证明,每个人、每个社会都生活在他者之中,我们都是他者的一部分。多么善良的蚂蚁!
在《仅存在一种发展模式吗?》中,列翁说,靠天吃饭的狩猎采集社会生活得更加悠闲轻松愉悦,摄取的蛋白质和热量也更多,并且十分均衡,相反,农业社会的劳动强度增大,但饮食质量反而下降了。萨林斯在他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中也做如是观。是的,原始人固然不能幸免于艰难的时刻,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维持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平衡。除了小部分阶段的突破以外,历史大部分时期是处于停滞状态的。列翁说,不是因为技术和物质发展,而是对声望、奢侈品和审美的追求导致了社会进化。换言之,发展的欲望造就了发展。
但任何发展都是双刃剑。供给肉食的动物所消耗的卡路里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它们所能提供的卡路里,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普遍恶化;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治疗需要),人类发明了将他人身上的物质注入自己体内的治疗手段(见《我们都是食人族》;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肉食需要),人类还疯狂地将草食动物改造成肉食、乃至同类相食的动物,从而导致了诸如疯牛病这样席卷文明世界的悲剧(见《疯牛病的教诲》)。发展导致了高度焦虑,发展把今天的人类都变成了食人族。
列翁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综合体。由于他的结构主义思维,列翁被后辈人类学家格尔茨称为理智至上主义者,一个标准的现代主义者;但同时,作为回忆录和游记作家的他,又写出了《忧郁的热带》这样弥漫着原始神秘主义的著作,他热切盼望着重返回不去的“冷社会”。作为同行,我深深地知道,列翁试图指出普遍的人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和原始人本质上其实毫无轩轾。只是因为,人类走到今天,或多或少走过些错路和弯路,才使得现代人和原始人貌似不可调和。
——本文选自《经济观察报·书评》/2016.9
好书荐读

《我们都是食人族》
(法)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著
廖惠瑛/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图片来源于网络,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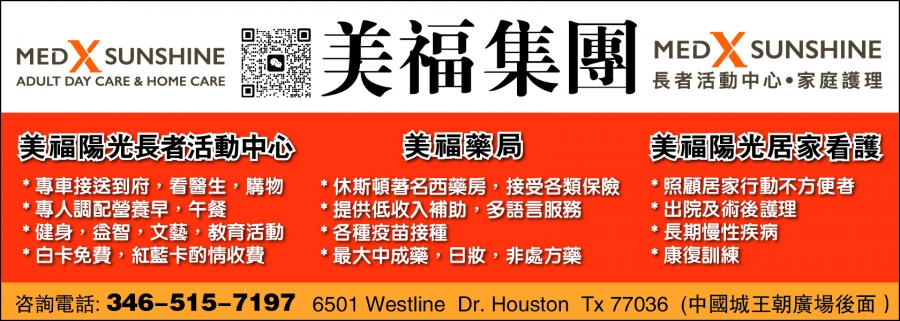


_1.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