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源于网络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法国史学大师,年鉴学派灵魂人物,曾获牛津、剑桥、芝加哥大学等颁授荣誉博士学位,并于1984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终生致力于文明史的研究,以其宏大的视野、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明快的文笔,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名,被誉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
《见识丛书·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是布罗代尔独力撰写的一部简明世界通史,旨在让年轻人对历史产生兴趣,让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该书从文明的角度,总览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按照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及总体史学观念,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注重对历史的洞察,对趋势的把握,由此探求整体的人类历史的深层意义。
英属印度时期(1757-1947年):一个古老的经济制度与现代西方相搏斗
✪ 费尔南·布罗代尔
16世纪时,葡萄牙人在远东建立了一系列商行。1498年5月17日,瓦斯科o达伽马到了加尔各答(Calicut);1510年,果阿被葡萄牙人占领。但葡属印度仅仅兴盛了不到一个世纪。
到了17世纪,在舞台上唱主角的已经是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工厂。甚至在法国人于1763年失败之前,1757年6月23日,罗伯特o克莱武在普拉西(Plassey,即Palassi,离今加尔各答不远)的胜利事实上已经宣告了英属印度的成立。它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存在到1947年印度独立;这样它存世的时间实际上与莫卧儿帝国相当。与莫卧儿帝国一样,它是一点点地发展起来的,直到1849年征服了旁遮普后才大功告成;同样,除其直接控制的地区之外,印度还存在着众多实行自治的邦国,土邦和公司。但是,在英国的统治下它们的独立地位与其说是一种事实,倒不如说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就总体而论,整个南亚次大陆都感受到了英国以巨大经济优势为后盾的咄咄逼人统治的冲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遥远的英国大致说来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商业和金融强国。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深刻影响了印度的所有的结构。
印度成为一个原材料的输出国。经营开发权掌握在东印度公司(直到1858年才解散)的手中,这种开发随着印度被征服地区的增加而加大。自最早的极度腐败的克莱武勋爵时期起(他在英国下院中遭到攻击,1774年自杀身亡),它就采取了三种形式剥削地方王公、商人和农民。
刚刚被征服的富裕省份孟加拉、比哈尔(Bihar)和奥里萨(Orissa)遭到残酷无情的盘剥。1784年之前在那里没有建立任何的秩序和公正,此后,出现了较为适当的统治。
在最早的这些年,劫掠和侵吞已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9月18日,印度总督康华里勋爵(LordCornwalis)这样写道:"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公司在印度斯坦拥有的土地有三分之一现在变成了丛林,只有野兽出没其中。"这基本上没有夸大。
确实,这些负有责任的新的统治者也是他们无力控制的历史进程的玩偶和受害者。人们提到的许多恶果,是在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建立货币经济时必须出现的,这里虽然很早之前就与世界贸易有着联系,但过去从不知道这么一种制度。英国的法律和西方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也事与愿违地带来了灾难。
不管怎样,一种历经艰辛取得、建立在印度遥远的过去之基础上的古老的稳定性,现在受到了严重冲击,在风雨中飘摇。
18世纪即将结束时,印度是一个由不计其数的村落和通常非常贫穷的农民构成的农业世界,一片片的草棚现在在马德拉斯(Madras)附近和其他不少地区仍可以看到。"
墙用晾干的泥坯砌成,房顶上交叉铺着棕榈叶,唯一的入口是一道低矮的门……用干牛粪作燃料燃烧起来的烟,尽其可能地从房顶的裂缝中冒出去。"但这些村落构成了联系紧密、稳定而自治自足的公社,它们由一个首领或长老议事会治理,这些人在有些地区甚至组织土地的重新分配。村子里也会有工匠,如铁匠、木匠、锯匠和金匠等,他们几百年来世代相传地从事同一种行当,换得的是实物报酬,分得村落收成的一部分。这些村落中有一些拥有奴隶,他们为较富裕的农民服务,负责饲养家畜、收拾家务和纺织。公社作为一个整体负担向邦国或最近的领主缴纳税收或者组织劳动。它们的收成和劳动有一部分用在别的地方,供印度政府控制的地处遥远的少数城市使用,从中却得不到任何回报。税收是城市与乡村之间保持的唯一的联系,后者无力购买城市进口或制造的任何物品。城市的工业产品仍然是奢侈品,供城市中少数居民使用,或供出口之用。但如果来自特权阶层的压力过于沉重,让人无法承受,村民就会逃亡,在别的地方寻求安身之地,希望能够得到好的运气。
村落的这种古老的生存经济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村子里既有农民也有工匠,因而除盐和铁外,它对外界的需求微乎其微,形成一个几乎封闭的系统……村落的社会组织建立在等级基础上,使所有村民各安其位,而与婆罗门(他们同时既是教师,又是祭司,也是天文学家)、长老或者属于较高种姓的较富有的村民保持距离。处于等级制最底层的是在田间劳动的不可接触者,他们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
这一整套制度先是在18世纪,而后是在19世纪日趋恶化。为了征税,英国人利用了原有的税收人员,但赋予他们对村落的所有权,此乃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这样,自孟加拉开始,就出现了一大批虚假的地主,即柴明达尔(zamindars)。柴明达尔的任务是向英国当局提供一定数量的税收,但为了确保其职位,他们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税额要高于规定数量。不久,他们不再在自己负责征税的地点生活,而雇用代理人负责此事。孟加拉的农民发现自己处在中间人和寄生虫的层层盘剥之下,负荷重得让人难以承受。
在没有任命柴明达尔的地方,英国人自己负责征税,这些税用现金支付。现在任何手头没有现钱的农民都不得不向高利贷主求救。这些高利贷主在印度各地兴盛起来。过去,他们不得不担心农民会反抗,对农民的愤怒心存忌惮;现在,法律在为他们撑腰,法官站在他们一边。如果农民欠债不还,他们可以牵走农民的牲畜,还可以拿走农民的田地。
可怜的农民,可怜ryot(印地语,农民)!由于地价在持续上涨,高利贷主有着各种便利条件变成地产主;另外,投机性的价格上涨也吸引投资商购买土地,把它作为保证收入的一种手段。结果是数量越来越多的大地产主通常对改良土壤不怎么关心,而只关心靠其收益生活。到了19世纪末,在一亿农民中可能有三分之一仍是小地产主,他们拥有的田地平均不到十亩,此为维持生存所需的田地最低限。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长老议事会十之有九不复存在(现在则正在复苏)。
由于下列原因,局势进一步恶化。
(1)由于来自英国和印度本土工业的竞争,乡村工匠遭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转为农民,从事田间劳动,而农民本身就已过多。
(2)英国资本家有系统地推行的双重政策:他们一方面把印度视为出售他们工业产品的一个市场(18世纪时,印度的染布或印花布在欧洲成为时尚,其非常古老的棉织业迅速发展起来。但如此一来,这一行业迅速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把这里变成购买某些原材料的市场,如孟加拉的黄麻,或孟买附近肥沃的黑棉土出产的棉花,由轮船运到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进行加工生产。
供出口的原材料由铁路运到港口。这些铁路早就建成了,它们在19世纪下半叶对印度内地造成了革命性冲击。单纯为了集散商品的城市兴起了。另外,印度越来越多的农民种植商品作物,这些作物不是供家庭或村落食用的。种植工业用作物的数量超过了食用作物种植量。旁遮普产粮区是个例外,但这里也出口其小麦。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在19世纪最后30年出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饥荒;虽然我们掌握的统计数字很不完善,但仍可以感受到,食品消费在普遍下降。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暴跌,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在地主和高利贷主手中。自由农民拥有土地的规模进一步萎缩,但其债务多得让人不可思议。农民因这一负担而受到严重削弱,他们相对于其债权人的地位比从前农奴相对于其主人的地位还要低。不管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多么大的自由,印度农民在经济上享有的自由越来越少。
现代工业出现的时间要晚,大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与最早的保护性关税同时。在那一时期,地方性工业的发展得到了众多有利因素的佐助: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带有大量无产者的现代城市的兴起,易于购买到原材料,最后是资本家的干预。
这些资本家来自三大集团。一个是帕西人(Parsis),他们是一千多年前从波斯逃到印度的琐罗亚斯德信徒的后代,主要居住在孟买地区。一个是马尔瓦尔人(Marwaris),他们是来自拉杰布达纳内地一个高级种姓,因其地区非常落后而免于受到英国人的竞争。第三大集团是来自古吉拉特邦的耆那教徒。
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三个工业城市:加尔各答(往东150英里),那里有塔塔集团(Tata,帕西人的一个家族)的钢铁冶炼业,且大量出产黄麻;孟买,棉织业和汽车装配中心;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位于靠北500千米处,是一个纯粹的棉织业中心。这些行业及其他行业,尤其是食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1942年后,像野草似的杂乱发展起来,而食物和纺织品的缺乏致使黑市价格疯涨,以致人们一度担心在日本的威胁面前,印度会完全覆灭。
1944年,工业家决定采纳孟买计划。这一半官方的计划过于乐观,它预见到大规模的投资因英国偿还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欠印度的债务而成为可能。该计划鼓励与英国工厂和商人达成协议,就像比拉(Birla)和纳菲尔德(Nuffield)在汽车生产方面达成的协议那样。此外,即便今天,在印度独立如此长时间之后,英国资本仍投资于加尔各答克莱武大街各银行所控制的许多行业……
这一工业高潮不过是加剧了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运动。塔米尔的一句谚语这样说:"如果你破产了,就跑到城市里去吧。"在那里的车间、工厂和家族服务方面(在那里得到的工资"虽然很少,但总比没有强"),能够找到就业机会。卡提阿瓦半岛的某些种姓之间及孟买富家招收厨子时,或者德干高原西南部沿海的穷人与孟买工厂中用手卷制香烟的手艺人之间,出现了不期而至的联系。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印度人的普遍忙乱,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
这样,甚至在独立之前,印度就已出现了人口众多的现代城市,这些城市有其肮脏的贫民区,如加尔各答的棚户区(bustees),更为有名的是孟买的分间出租的宿舍(chawls)或马德拉斯的切里(cheris),其泥墙与农村的土墙没有什么区别。
英国在1857-1858年的印度土兵叛乱后对其政策进行了反思。
这确实是英国修正自己对印度的整个态度,结束英属东印度公司统治(1858年9月1日),代之以在伦敦设立一个机构宏伟、权力很大的印度部(IndiaOffice),而在加尔各答设立一个副王取代从前东印度公司的总督的一个机会。
举例来说,英国人过去吞并印度从前属于王公的土地是不是太过匆忙了?
从现在开始,他们决定尊重地方自治;1881年,他们恢复了过去接管的迈索尔素丹国的独立地位,这是英国对印度采取新的态度的一个标志。
在这一五颜六色的印度世界中,如果他们不再直接进行统治,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小心地维持国家现有的区划并加以利用,尤其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大分裂。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分野必须在军队中加以维持。
关于这一问题,1858年埃尔芬斯通勋爵(Lord Elphinstone)用了一个重要隐喻,他说,大英势力的卫士是那些其安全因船体分为防水的舱室而得以确保的汽船。"我愿意按照同样的方针建构我们的印度大军,以确保我们印度帝国的安全。"也就是说,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喜马拉雅山区的锡克教徒,从此以后保持在不同的隔水舱里,永远不在同一个部门服役。
这些计划不久就被突发事件打乱。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场长时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到印度,造成了饥荒、瘟疫和农民起义。心怀好意的人民认为政权应实现自由,吸收某些印度教徒进入管理部门,甚至吸收他们到政府里来。
国大党的成员来自正在城市和大学中崭露头角的中产阶级,这些人越来越多地加入该党。他们既不是一个贵族或王公的阶层,也不是大地主阶层,后者深深置身于传统的过去之中,其社会保守主义与印度的主子非常相配。反过来,他们是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来源不同,因条件的变迁而出人头地。这一阶级中既包括帕西人、马尔瓦尔人和耆那教徒这样的资本家,也包括以实玛利的后裔穆斯林,以及那些其种姓具有政治使命的人,比如克什米尔的潘迪特家族,该家族与婆罗门有关联,在莫卧儿人统治时期出了不少政治家(现在该家族又出了位贾瓦哈拉尔o尼赫鲁,是今日印度的领导人)……圣雄甘地同样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该家族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产生过大臣,为古吉拉特邦卡提瓦半岛的小王公效劳。
在西方文明的吸引下,这些人在享受其好处的同时,既看到了其优势,也看到了其危险。比如,甘地的思想吸收了印度的非暴力传统、托尔斯泰充满激情的和平主义和耶稣基督的山上宝训……
印度的这一知识阶层在动荡不安的水域航行,梦想实现印度教可借以实现纯洁的某种宗教诸说混合。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印度不计其数的异端中获得了灵感。
——本文选自《见识丛书·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责编:笑笑
(图片来源于网络,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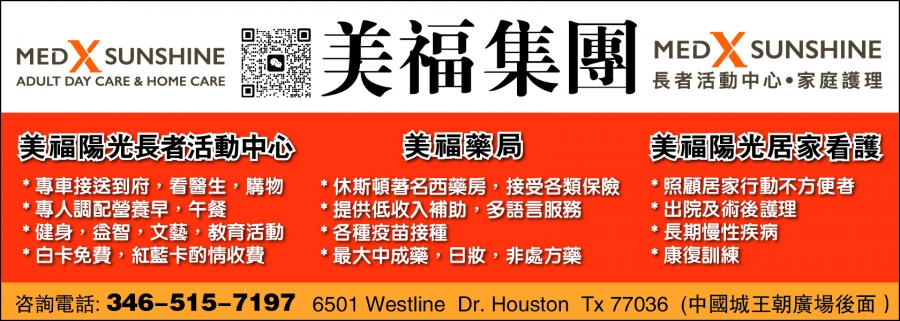


_1.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