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公里:巴黎圣母院,法国距离丈量的零点,一个民族的参照点,是起点也是终点,是法国总统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所说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当这座大教堂失火时,那么多人——无论是否是教徒——都在流泪。他们自身的一部分,他们的坐标,正在焚毁。
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圣母院在一场反对教权主义的狂热中遭到洗劫;到了19世纪,愤怒已经冷却,经过修复重建,它成为了举行帝王加冕典礼、民族解放运动和总统葬礼的场所,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成为法国与其动荡历史、君主制与共和制、宗教与世俗实现和解的地方。
几个世纪的光阴,证明了它的普世意义。无论是在法国还是法国之外,时间让它成为了每个人的大教堂。“我们所有人的一座记忆之矿,”在巴黎出生和长大的艺术家克莱尔·伊卢兹(Claire Illouz)说。
巴黎究竟是什么?是美。它的恐怖之处在于看着美丽燃烧,精致的塔尖倒在800年历史的横梁构成的火海里。这是集人类之大成者,如同神圣存在般强大的表达,在黑烟中化为灰烬。
人类生命的丧失是可怕的,但美的毁灭也许同样可怕。在一个充满焦虑、丑陋、仇恨和谎言的时代,这场大火让人感受到了不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约翰·济慈(John Keats)写道,“知道这个就够了。”
我的巴黎朋友萨拉·克利夫兰(Sarah Cleveland)给我写信说:“静得出奇,人们仿佛陷入了恍惚,看着火焰在大教堂墙内沸腾,像一口大锅。场面庄严肃穆。还有绝望。如此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竟然如此脆弱。”
文明是脆弱的。民主是脆弱的,就像那个尖顶。今天,对此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当一个普世参照物化为乌有时,一个深渊就打开了。
我还记得1976年夏天,我第一次住在巴黎的时候,教堂那如今已经向天空敞开的庞大内室是凉飕飕的。当时有热浪来袭。河流变成了涓涓细流,喷泉干涸,商店里的瓶装水销售一空。人们坐在教堂里的长椅上发愣。有人在祈祷。孩童在玩耍。后辈与长辈,愚者与智者,聚在一起。蓝色的光线透过入口上方华丽的彩色玻璃窗射了进来。空气中有石头和烛蜡的气息。
那神圣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包容。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庇护所,而在这个时代,美国总统在唾弃庇护之所,并考虑将贫困的移民丢给那些敢于自称庇护所的城市作为惩罚。
我在青年时代第一次看到的这座昏暗大教堂,是体谅人类犯下的错误的,比如1789年之后的那些革命者,他们误以为那些圣经中的国王是法国国王,于是砍掉了雕像的头颅。光阴荏苒,我的孩子们在圣母院的耳堂里玩耍。其中两个出生在巴黎,这座流光溢彩的砾石之城,它的小岛像一艘艘驶向桥梁的船,它的主干道由巴黎圣母院来锚定;这座大教堂总是在塞纳河的对岸,让人安心,它的外立面跟两座钟楼一样庄严,侧面像拱扶垛和滴水兽一样奇幻,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它都赫然耸立在眼前。
大火过后,我们的巴黎女士还在那里,她的塔楼已经没有了屋顶。马克龙总统发誓要重建大教堂。资金大量涌来。这位法国总统举止尊严,当这种尊严已从白宫消失之际,他提醒人们,尊严还具有令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
马克龙说,巴黎圣母院是“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想象”,换言之,它是一种记忆的方式,激励着所有追求某种超越的人。视自己为一切的特朗普总统的贡献是建议派遣“洒水飞机”灭火。他的建议被无视了。
也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就其代表国家的力量而言,最接近巴黎圣母院的东西就是由法国雕塑家创作的自由女神像。有一天,海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带来一种神奇的效果,自由的火炬仿佛脱离了雕像,在空中盘旋。看着眼前这一幕,我想象着把埃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的诗为特朗普时代而改写:
把你们的暴君、你们的富人,
你们企图溜走的可耻逃税者,
你们想偷东西的堕落败坏者交给我,
我要给他们自由。
把那些不体面的人交给我,看一看
像我这样败坏有多么容易。
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感觉到法国文明如此地重要。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未来几周,一旦第一波震颤过去,关于谁该对此负责、这场灾难是如何发生的、涉及了哪些疏忽,将会出现丑陋的争论。但在巴黎街头那些沉默、虔诚、唱着圣歌的人身上,我也看到了法国人团结起来,下定决心进行重建的可能——不仅要重建大教堂,还要重建一个被黄背心运动的暴力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分裂所动摇的国家。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是一个坚忍和重生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关于欧洲文明的故事。巴黎圣母院是从希特勒的手中幸存下来。如今它所呈现出的脆弱,同样需要欧洲的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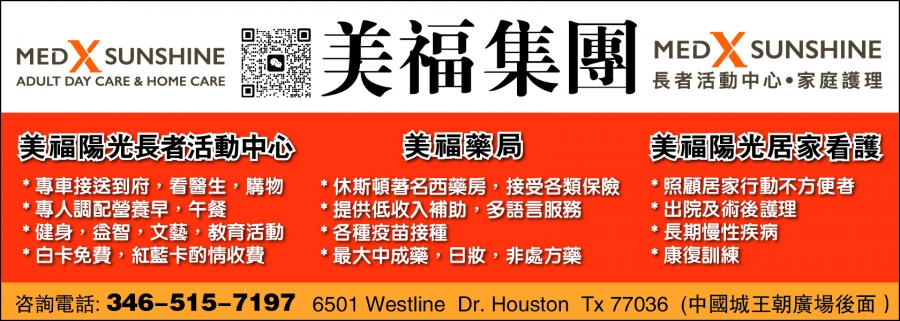


_1.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