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旭醫生
屈光手術和角膜病治療專家。影片「光明」(Sight)主角的原型。
近年來致力於幫助人們找到共同點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以臻至成功和幸福。
簡歷
愛爾眼科集團(Aier Eye Hospital Gr. Co.,全球最大的眼科集團)美國首席執行官。
王氏視覺學院(Wang Vision Institute)創辦人 。
田納西州范登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教授。
學歷
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醫學博士、優秀榮譽畢業生。
馬里蘭大學激光物理學博士。
中國科技大學化學學士。
社會參與
田納西州華商會創始會長。
田納西州移民和少數民族企業集團聯合創始人。
慈惠事業
王氏視覺復原基金會(Wang Foundation for Sight Restoration )。
著作與專利
自傳From Darkness to Sight《從黑暗到光明》。
十本眼科醫學教科書。
八項與眼科手術相關的專利。
獎項
美國眼科學會榮譽獎、美國華裔醫師協會終身成就獎、特雷維卡納撒勒大學榮譽博士學
位、NPR慈善家年度獎,以及基督教兒童會納什維爾年度獎等。
生平簡述
王明旭,祖籍福建泉州巿安海鎮,1960年出生於浙江杭州。祖傳醫學世家,自幼想要懸壺濟世,卻遭逢文化大革命,初二便無書可讀。為避免上山下鄉,他苦練二胡並習舞蹈,想考藝校,但當年卻不招生;自學作曲,投稿卻石沉大海;至終只得去工廠作小工。
1977年秋中國恢復高考。在父母鼓勵下,他花兩個月修完三年高中課程,以浙江省應屆畢業生高考前四名的成績,被中國科技大學錄取。求學之路從此開啟。
1982年2月他帶著五十美元踏上留學之旅,進入馬里蘭大學。1986年獲得博士學位後,為實現兒時從醫夢想,跨領域面對挑戰,竟取得美國醫學院入學考試最高分。他進入哈佛醫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聯合創辦的「健康科學與技術」專業,1991年獲得醫學博士。
1997年,范登堡大學邀請他擔任激光視力中心主任。2002年,他開創「王氏視覺學院」;2003年成立「王氏視覺復原基金會」,積極幫助全世界失明的孤兒。
王明旭醫生來自無神論背景,卻成為虔誠的基督徒。他是如何踏入信仰的?在過程中有什麼特殊經歷?又如何將科學與信仰相互融合?《恩福》雜誌主編陳宗清牧師詳讀了王醫生2016年出版的自傳《從黑暗到光明》,並觀賞了電影「光明」的預演,於7月6日與王醫生會晤,對他進行了專訪。
小時對基督信仰的接觸
陳:王醫生的祖籍福建安海鎮,介於泉州和廈門之間。在18、19世紀時,那附近就已經有不少人聽到過福音。請問你的祖父和長輩是否有機會接觸基督教信仰?
王:我的祖母是虔誠的佛教徒。記得小時候每次回閩南,都看到家族的大堂中陳列著祖先的照片。從清朝開始,每一代的主要家長都有一塊小牌子。距離老家不遠有一座廟,祖母常會帶我去那裡頂禮膜拜。我們家族從曾祖父開始就行醫,不過是中醫;我父親是第一個西醫。我沒有印象親友中有人信基督教。
陳:你什麼時候第一次知道基督教?
王:我對基督教的認識,主要是來自西方的小說。在文革時期,所有西方小說都是非法的,一般人沒有機會讀到。但幸運的是,在我們家,父親把毛澤東的「紅寶書」和宣傳畫擺在外邊,卻在它們的背後藏了兩類書。一類是中國的古典名著,如《三國演義》、李白杜甫的詩等等;另一類是西方的小說,例如《紅與黑》、《戰爭與和平》等,其中有提到教堂、神父等。這是我對西方宗教最初的認識。
印象較深的是,這些宗教和信仰的元素與共產主義的教導截然不同。共產政府下命令,給規則,必須去遵守;而小說中的信仰元素則好像在探索和體現生命的意義,給予了我思考與想像的空間。
對上帝的初探
陳:你在中國科技大學讀化學,但是到馬里蘭大學讀研究生時,卻轉到激光物理,為什麼會這樣選擇?
王:我很小就想要當醫生,繼承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志向。然而,在文革期間卻連高中都不能讀。當時我學二胡和舞蹈,想要進文宣隊,以避免上山下鄉的命運。1977年迎來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過去十年曾經讀過高中的人,從全國各地回來參加,應考的人數非常龐大,情況很亂。當時對我而言,實在是背水一戰。我處於失學的黑暗狀態已有兩三年了,要去參加高考,當然只有拼命苦讀。當時沒有錢,也找不到複習材料;父母幫了我很多,他們找到1964到1965年的考卷,抄在紙上,讓我複習。我日以繼夜地努力,後來終於考上大學。
我原本想讀醫學院,但那一年並沒有按照學生填的志願分發,而是由各大學按成績挑選。於是我就被中國科技大學招入化學系。後來我去美國讀研究所的時候,就選擇激光物理學,因為那時我已經想要成為一名激光眼科醫生。大部分醫生都是讀醫學院的,技術方面的培訓並不足夠。我曲折迂迴的求學經歷,反而彌補了這一弱點。
陳:傳記第八章「黃色的點」(Yellow Dot)中,第一次提及上帝和信仰。那時你和聞納教授(John Weiner)一起做一個與你的激光物理學博士論文相關的實驗。當時你為什麼會想到上帝?
王:那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實驗。我們用盡了所有的科學定律,卻不起作用。我已經來到自己能力的極限,沒有任何辦法了。就在那時,我想到小時候讀過的西方小說,裡面提到有上帝。於是,我想作最後一搏,試一下禱告:「如果真的有上帝,請你來幫助我。我想看到神蹟,就是現在這當下!」不可思議的事竟然發生了!我看到了一個從未看到的現象——在氣體室(gas chamber)的中間,有一個「黃色的點」正在發著光芒。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們終於讓原子對撞機開始工作了。當時聞納教授興奮地跪倒在地上,快樂得就像過聖誕節的孩子!
不過,那一次對上帝的經歷,對我而言更像是一種好奇心得到滿足,還不能算是深刻的信仰。
無法否認的創造主
陳:你一生中經歷了許多艱難。特別是在文革的那幾年,你沒辦法讀書,感到非常黑暗與挫敗。那時你曾經想到過上帝嗎?
王:那時候倒沒有想到。當時我的想法只是:我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否則就會持續生活在黑暗中。但有意思的是,正因為如此,我給了自己進入學術大門的機會,以致後來能去探索是否真的有上帝。
前面提到的實驗,是我對上帝一次好奇心的火花迸發。後來我成為醫生,做過許多極其艱難的手術,影片中卡嘉爾(Kajal)和馬麗亞(Maria)的個案就是例子。這些挑戰對我影響很大,促使我一步一步深入思考,並且愈來愈體會,一切都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的作為。
陳:讀醫學時,你是否發現人體非常奇妙,特別是眼睛如此奧妙,很難用無神論的隨機產生說來解釋,從而感到有神的創造論比較合理?
王:達爾文的進化論曾經就是我的「聖經」——這是無神論科學家的根基。然而我在醫學領域學習越多有關眼睛的知識,就越覺得奇妙。
眼睛要看得見,必需首先由水晶體、視網膜來感受光,再透過視網膜的神經處理,經過視覺通道,來到大腦皮層,在那裡捕捉信號,並進行圖像儲存、信息處理、決策與描述等等。整個過程中需要各式各樣的細胞,數量非常驚人。
人的胚胎從單細胞開始,十個月後發展成為嬰兒。視覺系統在期間完整生成,其中的細胞排序要全部正確;如果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視覺就不能運作。雖然有些孩子天生有一些小問題,但大部分人的視覺都是正常的。人的視力發生過程真是非常神奇。
後來,我重新翻開達爾文的書,發現他自己談及,他的進化理論中最弱的一環,是很難應用在人的眼睛上。這是他最不能解釋的。因為純粹的進化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發展得那麼完全。幾百年前的達爾文居然和我有同樣的疑問!
如果說,幼年時西方小說中的信仰元素引起了我的好奇,而「黃色的點」燃起了我相信有神的火花,那麼當我進入醫學研究時,對神就開始有真實的尋索了。
陳:傳記中提及,韓德博士(Stanley Hand)曾在信仰上幫助過你。這位虔誠的基督徒是怎樣引導你的?
王:韓德博士在信仰上對我的幫助,主要是兩方面。有一次他帶我去吃飯,聊到信仰的話題。他指著對面停的一輛車子問我:「汽車和人類大腦的區別是什麼?」我說:「人類大腦比汽車複雜得多了。」他說:「一堆爛鐵可能自己組裝成為汽車嗎?」我說:「不可能。」他說:「那麼,人類的大腦呢?」他的話引起我很多思考。
眼睛那麼複雜,卻又那麼有序,一個細胞都不掉隊。由此看來,這一切都不可能是隨機的,而是出於一位設計者。韓德博士幫助了我確定信仰的第一步:肯定有上帝,祂是創造主和總設計師。
後來,韓德博士送給我聖經,那是我的第一本聖經。他告訴我,宇宙不僅有神,而且是位獨一的真神。我從新約開始讀,逐漸明白耶穌的偉大奇妙;祂復活的見證在歷史上證據確鑿,讓我信服。
信仰經歷柳暗花明
陳:傳記中提到,你曾與一位敬虔且熱心的基督徒女醫師葛文(Gwen)交往,前後五年。她還到過中國宣教。她幫助你對信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在那段時間內,有人帶領你真正認罪悔改,接受基督作為救主嗎?最後促成你想要受洗成為基督徒的因素是甚麼?
王:在認識葛文之前,我已經開始讀聖經,也自認為是基督徒。我逐步意識到,科學與信仰兩方面都是必需的,缺一不可。科學能改善人的生活,而信仰則提供了人生的意義與方向。過去,我獨自在人生中摸索尋找神;認識葛文以後,她帶我參加基督徒醫療人員的團契,認識了許多基督徒醫生,這些醫生的信仰經歷對我很有啟發。
我在那裡常聽信木斯博士(Simms)講道,後來請他為我施洗。他是從事基督徒醫學事工的牧師,在我信主的過程中,他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陳:你和葛文的交往,後來遭到她母親的堅決反對。她母親也是信徒,卻因你是華人而無法接受你。這件事有沒有影響你對神的信心?
王:有的。我和葛文的交往非常愉快,兩情相悅,且論及婚嫁;然而後來卻受到葛文母親的強烈反對。遭到這樣的拒絕,讓我充滿痛苦與失望。我驚訝地發現,竟然有些基督徒不按信仰的原則生活。這令信主不久的我感到震驚,甚至一度覺得基督教有問題。
然而,我慢慢認識到,基督徒和基督信仰是不同的。就好比一間教會,如果牧師沒有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們應該質疑的是他本人,而不是整個基督信仰。
陳:傳記中詳述了幾個眼睛手術的個案,每回難度都極高。手術之前,你和同事總是迫切禱告,把一切交在神的掌管中。多數手術都很成功,然而其中印度小女孩卡嘉爾的個案卻是例外。雖然她的目盲並未恢復,但她的心靈卻得到醫治,體會人和神對她的愛。請分享在這些過程中,你對信仰的體會。
王:我2015年寫自傳時,已經作過好些手術,其中四個案例特別成功。我在其中所學到的功課是:在遇到挑戰時要信靠神,要心存盼望,堅心相信會有美好的結果。有些基督徒以為,既然信靠神,就可以悠閒面對生活,甚至於懶惰;但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必須盡心盡力去作研究,注意一切細節,將自己的潛力發揮到最大,而上帝會讓我做得更好。
不過,卡嘉爾的案例讓我學到非常不同的功課。她眼睛的情況非常糟糕,4歲時因被繼母用硫酸倒入雙目,眼內的組織幾乎破壞盡淨,沒有什麼可以用來作修補。手術之前我們盡力去預備,也有許多人為她禱告;但手術之後,她只看見一點光,卻沒有恢復視力。很多人紛紛來詢問:「她明天是否能看到?」我們卻必須報告壞消息。
那一次的失敗,我經歷到基督徒常遇見的兩個大問題:為什麼神會允許壞事發生?為什麼神沒有回應我們的禱告?手術失敗後,我對神相當憤怒不滿,信心極大動搖。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類似的經歷——我們能否在神不回應禱告的情況下,依然堅持信仰呢?
王氏視覺復原基金會每年都舉辦一次「眼睛舞會(Eye Ball)」,為失明的孤兒籌款。那年我們邀請卡嘉爾作嘉賓。當時我自己的內心對信仰仍然很失望。然而,有個11歲的男孩來到舞會,卡嘉爾在美國時寄宿在他家,他們經常在一起玩。那個男孩起來發言說:「雖然卡嘉爾看不到,但我們總是看到她在笑,她是那樣開心。」男孩抬頭向他父親說:「爹地,我和卡嘉爾在一起,再也不需要玩iPod了。」此情此景讓我非常感動。卡嘉爾的喜樂對周圍的人有那麼大的感染力,這喜樂來自哪裡呢?是出自她裡面的生命。
那天晚上,我將麥克風遞給卡嘉爾,要她分享幾句。她拿著麥克風就笑了。她到美國後學了英語,我以為她會用英語說幾句,結果她卻問我:「我可以唱歌嗎?」原來她要的不是看見,而是唱歌!可能因為她被遺棄,是因為繼母發現她不太會唱歌,無法成為能替她掙錢的盲眼小乞丐。
她用天真的童音唱著:「耶穌愛我,我知道。」現場五百餘來賓,很多人流下了眼淚。那是2007年的事,有位記者抓拍了這動人的一幕,後來這張照片流傳到很多國家。
這件事讓我深深體會到,原來,神是會回應我們禱告的,但卻是「以祂的方式,在祂的時間」(in HIS way and at HIS time)。我學到,我們對神最終極的見證,不是人所謂的成功,而是神自己的作為。雖然神沒有攔阻卡嘉爾受苦,但卻藉著她內心的喜樂傳遞了生命之光。
每個病例都給我不同的體驗,許多病人的信心也帶給我幫助。透過我的傳記《從黑暗到光明》,我想要呈現人生的兩個平行線。第一,失明的人通過手術,可以經歷從黑暗到光明。然而第二層更深的意義是:心靈落入黑暗的人,可以通過信仰進入光明。
擴展神的國度
陳:請談談此次獲獎的電影「光明」(Sight)。我們可以如何鼓勵美國華人基督徒,十月時邀請慕道友去看這部電影,讓它能影響更多人?
王:很高興影片「光明」獲得了2023年國際基督教視覺媒體的「最佳影片獎」,在兩百多部參展影片中脫穎而出。這實在是十分難得。主辦單位向我透露,他們選擇這部片子的原因,是因它講述的故事能打動一般的觀眾,不是只讓信徒感到對信仰沾沾自喜。
過去許多基督教電影雖常以佈道為目的,但就像一篇講道信息,往往很難吸引非信徒和懷疑者。可是這部電影沒有說教意味,呈現的是真實故事。
我特別推薦這個影片給兩個群體。第一,我們下一代的孩子。美國的年輕人正在離開教會;統計顯示,小時候上教會的年輕人,進入大學之後,75%都離開教會。這是很嚴重的事。許多孩子們認為,隨著科技發展,他們已經不需要上帝。這部電影會告訴他們,科學雖然是必需的,但並不足夠。科學給予工具,但可能帶來好處或者壞處;我們更加需要的是基督,唯有祂才能指引我們人生的道路與方向。
第二個群體是慕道友、非信徒和懷疑者。希望這部電影能激發他們對上帝和信仰的思考和探求。
我們有點擔心,可能並不是太多基督徒願意去看這部電影,因為影片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信徒自我感覺良好。這個故事反倒是讓基督徒謙卑下來,願意去尋找與未信者的共同點,與他們對話。這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目前這部影片在環球影院只有10月27日一個週末的放映時段。但如果票房很好,就可以有更長的放映時間和更多的放映地點。所以需要朋友們幫忙推薦。
陳:願神祝福使用這部影片,感動許多人。在信仰方面,王醫生還有什麼想與我們分享?
王:在這個非常分化的世界,「尋找共同點」,幫助人們互相瞭解與合作,為社會帶來福祉,是我個人這些年來努力的方向。這部影片也是希望能促成這個目標。
我1997年到田納西州後,一直參加的教會是伯特利世界遍傳教會(Bethel World Outreach Church),我也參與教會的拓展事工。我們的牧者布魯克斯牧師(Rice Broocks)很看重影視,他寫了《神沒死》(God’s Not Dead)一書,後來拍成很叫座的電影。片中有位中國學生,是以我為原型。他和我一起為「光明」影片寫了查經材料。我也成立了「共同點網絡」(Common Ground Network)。希望更多人來一起推動,擴展神的國度。
陳宗清訪問
程嫣、劉良淑文稿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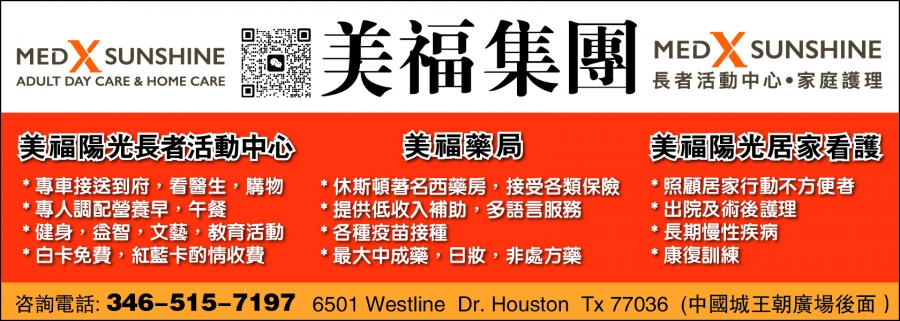


_1.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