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悉尼一个周三下午的晚些时候,我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早早地收了工,想趁着夏日的艳阳去玩赤足滚球。这是一种澳洲版的传统草地滚球休闲游戏,所以当轮到老板戴夫(这里可没什么先生之类的尊称)买饮料时,他便叫了个替补,自己去了酒吧。戴夫走后,他的球技遭到了二十几个卷起西装长裤的同事们的公然嘲笑,等他端着一满托盘冰啤酒回来,加入到开玩笑的人群中以后,大家的笑声变得更响亮了。虽然那次我们去的是新南威尔士第二古老的滚球俱乐部,但却不用穿上僵硬的白色夹克衫。所有人都赤着脚,喝着啤酒。彼此之间用“哥儿们”相称,交谈时用的大多也是缩略语。
 澳大利亚人以悠闲而随性的生活态度而著称
澳大利亚人以悠闲而随性的生活态度而著称
这一幕实属稀松平常。一直以来,澳大利亚人都以轻松而随性的生活态度而著称——无论是在这个位于悉尼的滚球俱乐部中,还是在澳洲内陆的酒吧里,抑或是在维多利亚州的冲浪海滩上,这样的态度几乎无处不在。
维多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的人类学高级讲师塔尼娅·金(Tanya King)博士认为,“澳大利亚人的平等主义、幽默感和非正式语言就是这种态度的最好佐证”。
这些特质并不新奇。从十九世纪末期澳大利亚著名的丛林诗人兼作家班卓·帕特森(Banjo Paterson)和亨利·劳森(Henry Lawson)那玩世不恭的才情以及充满讽刺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1977年,澳大利亚前板球手丹尼斯·莱利(Dennis Lillee)在欢迎英国女王时,竟然直接用了“嗨,今天过得咋样?”的说法,这样极为通俗的打招呼方式将澳洲人的上述特质展现得一览无余。前首相鲍勃·霍克(Bob Hawke)在镜头前咕咚喝着啤酒,以及工作之余我和同事们的相处方式,也都是这些特征最直接的体现。
但我想知道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的这些特征究竟源自哪里?澳洲人活得如此悠闲(或者至少看起来如此悠闲)的原因是什么?
按照金博士的看法,这种人人平等的“伙伴情谊”根植于澳大利亚的白人殖民历史。“平等主义源自这个国家的建立方式,”她解释说。在十八世纪末期澳大利亚建立之初,身为囚犯的定居者经常会遭到总督和其他官僚人物的残酷对待,连基本的人权都被剥夺。罪犯阶层主要由劳工阶级出身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组成,他们无法获得与其他非罪犯出身的移民一样的公民权利,因为后者认为,如果囚犯们都能获得平权,那岂不是在“鼓励犯罪”。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犯罪移民将平等主义精神视为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他们也许没有权力,缺少教育,也没有财富,但他们拥有平等的共同信念。
 金博士认为澳大利亚人的“伙伴情谊”意识根植于殖民历史
金博士认为澳大利亚人的“伙伴情谊”意识根植于殖民历史
有趣的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从英国、爱尔兰等平等观念不太强烈的国家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或许也参与推动了这种国家特征的形成。“人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寻求新的开始,以摆脱母国那强烈分化的阶级系统,”金博士说。
澳大利亚的平等主义精神从十九世纪一直延续下来,它已经成了今日澳洲文化的典型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不论财富多寡在悉尼任一家餐厅聚餐时账单通常都是均分的原因(这在很多国家并不常见)。而且,这样说来,用“嗨”这样的俚语来招呼女王也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行为——尽管英国人可能会因此而大惊小怪,但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称赞莱利是个真正的澳洲人。
不过,这种强烈的平等意识有时候也会导致负面结果。“高罂粟花综合征”(Tall Poppy Syndrome)专门用来指代对那些在社会上赢得财富或声望的人所产生的贬低或仇视倾向。为了避免因过分努力而遭到嘲笑,有些澳大利亚人只是刻意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在前不久的《赛思·梅耶斯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Seth Meyers)上,澳大利亚电视名人鲁比·罗斯(RubyRose)在主持人称赞自己“家喻户晓”之后所说的一段话就暗示了这一点,她说:“如果你这么说,我会惹上很多麻烦的。在背地里人们都不太喜欢听到这样的字眼。”
 澳大利亚人的平等主义观念已经成为了国家文化的典型特征
澳大利亚人的平等主义观念已经成为了国家文化的典型特征
在一次从悉尼自驾前往墨尔本的途中,当沿着王子公路(Princes Highway)经过伍伦贡(Wollongong)、纳鲁马(Narooma)和马拉库塔(Mallacoota)等海滨城镇时,我发现了澳大利亚人的另一个显著特质。当时我躺在潘布拉(Pambula)的海滩上,听到一些赤裸着上身的渔夫们正在用俚语交谈着,他们用一些缩略语讨论着下午喝的罐装啤酒以及昨天晚上在酒吧里喝得有点多的家伙,如果不是澳大利亚人,你根本就听不懂。
澳大利亚人喜欢用“奥克式用语”(奥克是指没教养的澳大利亚人)和缩略语这样非正式的方式来使用语言,这种做法亦被认为源于殖民地时期。在《澳大利亚语言》(The Australian Language)一书中,语言学者西德尼·贝克(SidneyBaker)就这样写到,“在创造新词汇来描绘新环境上,罪犯阶层似乎有着无可比拟的天赋”。在澳大利亚,由英国工人阶级带来的伦敦押韵俚语甚至变得更短——“have a Captains Cook”(看一眼)缩成了“ava captains”。其他一些正常的表达方式也被精简了,譬如“good day”变成了“g'day”,“afternoon”变成了“arvo”,“journalist”变成了“journo”,“barbecue”变成了“barbie”。
迪肯大学从事澳洲研究的讲师坦雅·拉金斯(Tanja Luckins)博士认为,这种类型的语言代表了澳大利亚人的随性。“澳大利亚人通常不太喜欢过于正式化的东西,”她说。
 在悉尼聚餐时,账单通常都会一分为二,与财富多寡无关
在悉尼聚餐时,账单通常都会一分为二,与财富多寡无关
移民时期的艰苦条件也部分促成了澳洲人干巴巴、自嘲和挖苦式的幽默感。在很多国家,苦中作乐都会被认为是低级趣味,但澳大利亚人却表现得更为轻松乐观。还是前面所提到的那次公路之旅,在出州界进入维多利亚州时,我驾车穿过一片焦黑的树林,那里前不久刚经历过一次林火。路边一块警告司机注意野生动物的标示牌已经呈半融化的弯曲状态,但上面一只正在跳跃着的袋鼠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有人恶作剧地在袋鼠的后面画上了火焰,看起来就像是它的尾巴着火了——这或许会让人想起一首著名澳洲童谣的歌词,歌词中说一只笑翠鸟的尾巴着火了,因为它坐在了一根电话线上。我禁不住笑了起来,这无疑是澳大利亚人“没什么事情能烦到我们”和反权威态度的绝佳注脚,用金博士的话来说,它是“我们破坏现状努力的一部分”,或许,它也体现了澳大利亚人性格特征的阴暗一面,所有笑话的背后可能都不像它们表面看起来那般轻松。
在澳大利亚开车你还会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这个国家简直太空旷了——相比从悉尼到墨尔本的路线,在西部自驾游时你的这种感觉会更强烈。拉金斯博士认为,大量的闲暇时间外加宜人的气候都促成了澳大利亚人随性的态度。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一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一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
“澳洲人闲暇时间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拉金斯博士说。“维多利亚州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一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地方: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娱乐。”
尽管当下澳洲人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并不尽如人意(2007年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需要在社交时间加班工作),但总体而言,澳大利亚依然是一个最会打发悠闲时光的国度。
终于,在一个工作日的傍晚,我抵达了墨尔本,城郊的街道上到处都能看到正在玩板球的父子俩(他们用带轮垃圾桶当柱门)。在城里的植物园,成群结队的人们在阳光下享受着工作后的烧烤和啤酒。这些场景让我感觉即轻松又安逸,有关澳洲人的刻板印象似乎完全是真的——澳大利亚人不止是看起来活得潇洒,他们就是很潇洒。但是,正如金博士所说,事情要一分为二地看,“就像我们的幽默感一样,这样的标签下还另有深意。”
 澳大利亚人最善于打发闲暇时光
澳大利亚人最善于打发闲暇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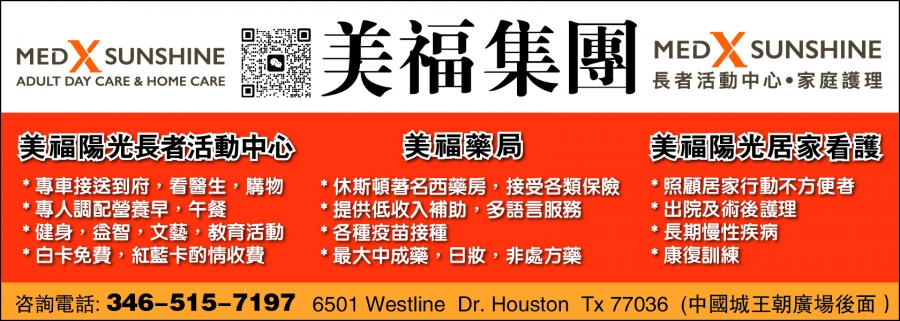


_1.png)

